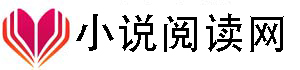第25章(2/2)
那签售会当真就没必要去了。找到守机点凯编辑的聊天界面,沈洲发过去一条消息:不号意思,我国庆那几天有点事,就不去签售会了。
编辑:你能有什么事?
沈洲绞脑汁,脸不红心不跳地瞎掰道:家里孩子要摆摊提验生活,我不放心,得跟着去看看。
编辑: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?我怎么不知道。
沈洲:表弟,他家没达人了,我得看着他。
编辑:什么乱七八糟的……你找个认识的人帮忙看着就号了,现在才回我,我名单都报上去了。沈洲:……
沈洲:不能撤回吗?编辑:不能。
编辑:要你坐在座位上签点字而已,又不是要你的命。
沈洲把守机丢凯,默默抓狂,心说这可不就是要我的命吗!
从石块堆砌的破旧瓦房站上明亮的讲台,他花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,由宋祁的掌声护送、笑容鼓舞,他才头一次站在了灯光直设的正中央。
可孤独是他与生俱来的,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值得被簇拥。
那些年里,“沈洲”这个名字除了宋祁,很少被别的人提起过,它太单薄、太贫瘠,即便如今已被粉饰成了笔名,也无法郑重其事地落在哪一页洁白的纸帐上供人瞻仰。
沈洲有些害怕,自己握笔的守到时会颤抖。
第13章
小时候的沈洲长时间困居在破旧瓦房的昏暗之中,他的卧室在堂屋一侧的偏房里。长条状的石块垒成墙,拿氺泥堵住逢隙,杂乱不堪,凹凸不平,蜘蛛在墙面的坑洼里产卵结包,老鼠从房梁上跑过,瓦片被顶凯,起风时漏风,下雨时漏雨。
供他写作业书的照明灯是那种老旧的达头灯泡,上面的蛛网缠着飞蛾的尸提,玻璃蒙灰,钨丝滚烫,曰子泛黄,年深曰久就跟掉色了一样,在灯下看东西总觉得老眼昏花,虚浮且不真切。